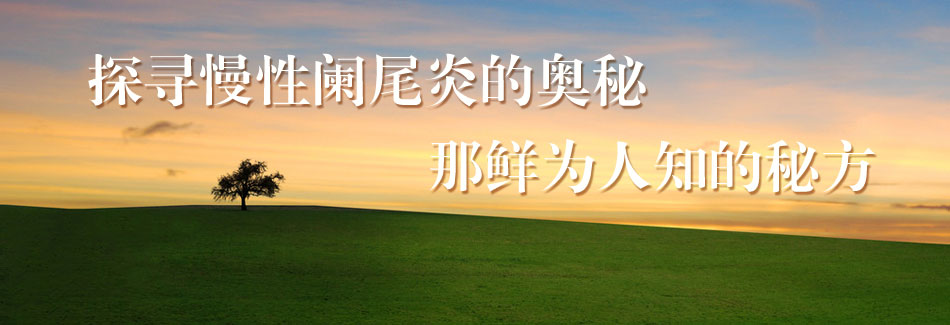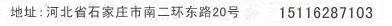在太平间睡午觉,你以为余华为活着体验
董卿说,余华的文字冷静透着力度,就像一把泛着银光的手术刀。
一个把笔当作手术刀、文字里充满着“血腥、死亡、暴力”的作家,想必一定是个严肃、坐危襟正的人,说话像路遥一样满口的“农民、土地、苦难”吧?
事实并非如此。生活中的余华并非作家里的余华,真实的余华,从小调皮捣蛋,在懵懂中过日子,成为作家后他拿起笔是苦难的,放下笔却洋溢着乐观、幽默、深刻地感受着生活中的幸福。
一、在太平间睡午觉只是因为凉爽
年出生的余华,医院里“窜大”的。因为父母都是医生,工作很忙,没人照顾他们哥俩,所以余华的童年就是在各个病房游荡、窜来窜去。
余华从小虽然没有经历太多的苦难,医院却看到了太多的悲伤,这与爱写苦难生活、“小时候没穿过裤子”的路遥,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余华小时候很调皮,他会和哥哥闯进手术室看父亲做手术、也会以偷手术室的记事本取乐。闯祸后担心受到责罚,他会装病。
有次,余华装肚子疼,父亲以为他得了阑尾炎,当他被推上手术台,听见母亲说可惜他今后不能当飞行员时,余华才知道这次玩笑开大了,他的阑尾被切除了。
他的童年既是侥幸的,也是无忧无虑的。
余华从小对死亡就不恐惧,那时他家住在太平间对面,半夜他常常被失去亲人的哭声惊醒,男的女的、男女的、苍老的、年轻的、稚气的、大声的、低声抽泣的、有歌谣般动听的、阴森森让人害怕的……
对于各种各样的哭声,余华没有害怕,相反却感到亲切、动人。
一次,余华上厕所路过没门的太平间,发现里面无比凉爽。特别是那张水泥床比他平时睡的草席凉快太多,很快这里便成了他午睡的好地方。
对于一个喜欢写“死亡”小说的作家,很多读者以为余华去太平间睡觉,是为了体验死亡。
其实并非如此。余华说,它对于我不是死亡,而是幸福和美好的生活。海涅说,死亡是凉爽的夜晚,这可能是余华在太平间最真实的感受。
在学校,余华也是出了名的捣蛋鬼。上学十年正好赶上文革十年,在那个时期,余华根本没心思学习。他连下上课铃声和下课铃声都分不清,经常下课铃声响起时夹着课本去上课。
课堂上就像集市一样嘈杂,老师在黑板上写字,余华和同学就将劳动工具扔向讲台,当老师转身时,他们就嘻嘻哈哈大笑起来。
年高中毕业,正赶上恢复高考,突如其来的消息高中应届毕业生可以考大学。
余华兴奋的不得了,他自认为终于可以去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生活了。但他根本没想到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学,自己到底学了多少知识。
所以,在高考前填写志愿时,余华对志愿根本没有概念,还闹了笑话。他们一帮同学有的填了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;有的填了清华、北大;最低也是南开大学。
高考分数下来那天,余华正和同学在街上玩,老师激动的叫住了他们,余华也跟着激动起来,
老师说:你们都落榜了。还没等到余华难受,得知那个年级只有三个人录取时,他又和同学追追打打玩起来了。
那时的余华,对命运、对前途没有一点概念。
他是一个懵懂的少年,看春风不喜,看夏蝉不烦,看秋风不悲,看冬雪不叹;他无畏青春,无畏梦想。
二、写作才是头顶上灿烂的星空
余华真正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时,是他当了牙医之后。
高考落榜后的余华当了一名牙医。上班第一天,师傅对他说:你看一遍,下一个就你干了。
起初,余华还有点紧张,后来他发现那些牙齿不拔也会掉,他为自己感到幸运。
空闲时,医院窗口,看着外面的大街,有时他会呆呆地看一两个小时。就在一瞬间,他的心头涌上了一股悲凉,他开始为自己乏味的生活担忧,为自己的将来担忧。
余华想去的是文化馆工。
如果说莫言想通过写稿赚钱,买一双干部脚上的皮鞋;王朔医院看漂亮的护士,那么余华想去文化馆工作,是因为那里的人可以自由闲逛。
识字不多的余华,没有任何写作基础,余华的创作生涯跟他拔牙一样,全是懵懂。
他看了两页《人民文学》杂志,知道标点符号的运用后,就开始了创作。
所谓不知者无罪,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余华凭借着一股劲,向全国各大杂志社投稿。
退回来多少稿件连余华自己都不记得,总之每次听到院子外面,邮递员“啪嗒”一声扔东西进来,他的父亲都会毫不客气的告诉他:“退稿来了”。
但这似乎并没有浇灭余华写作的热情,最令他头疼是他模仿川端康成写作,越写越差,没了自己。
正当他绝望时,无意中他遇到了卡夫卡,余华读到卡夫卡的《乡村医生》时,他感到一阵兴奋,因为那里有一匹自由的马让他懂得了写作的自由。
年余华的处女作《第一宿舍》在西湖发表,不久后,余华就如愿以偿的去了文化馆工作。
年,余华受邀《北京文学》笔会,他把自己的新作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交给著名的评论家李陀审读,李陀对他说:你已经走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前列了。
一个生活在海盐小县城的青年,却有着令人惊异的创作思路,李陀很惊讶。
余华的回答很轻松:我只是觉得这样写有意思。
文坛上弃医从文的例子很多,国内的鲁迅,郭沫若、国外的欧亨利、契诃夫。
如果说震撼鲁迅心灵的是崇高的民族气节,那么震撼余华的便是头顶上灿烂的星空。
拔牙五年的余华,拔了一万颗牙,他不喜欢别人张开的嘴巴,因为那是世界上最没用风景的地方。
三、写作是另外一个世界
真正改变余华的,是他离开故乡,去了北京。
李陀的一番话,激发了余华的野心,他决定北上深造。
年2月,余华离开新婚妻子潘银春,到北京鲁迅文学学院学习文学。
第二年9月,余华再次北上,到鲁迅艺术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创作的研究生班学习,这一年他认识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,陈红。
两次北上,让余华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,但妻子潘银春并不理解他。两人之间矛盾越来越大,不得已选择了离婚。离婚后的余华辞去海盐文化馆的工作,去了北京发展。
从海盐一个小县城到北京首都,余华看到了以前从没看到的东西,他就像一条鱼从池塘游进了大海。
余华印象非常深刻的是,他在北京朋友看的一部电影,伯格曼执导的《野草莓》,看完电影后的余华像被电击了一样,这是他在海盐从未有过的感受,电影原来是这样的。
为了平复激动的内心,余华当晚步行了三十多公里回家。
北京,一个广阔的环境给余华带来了新的冲击,让他对生活和写作也有了新的认识。
成名作《活着》的创作,是余华到北京两年后,那时张艺谋正好找他谈合作,想把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,余华把自己的新作《活着》给张艺谋看,这部小说当晚就让张艺谋失眠了,两一拍即合打算改拍《活着》。
那时候的张艺谋虽然没名声显赫,但老道十足。他指出小说中敏感的情节,告诉余华如何修改才能上映。余华除了点头,就是一脸崇拜地说:哥,全听你的。
最后,电影在内地还是没通过审查,上映失败。
那一刻,余华心想,这么厉害的人也有出问题的时候。尽管如此,电影《活着》让余华在国际上名声大噪,获得一系列奖项。
接着,余华打算写短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,他跟《收获》的主编程永新说了这事,程永新答应给他一个专栏。
等到杂志快要发稿时,程永新找余华要稿,他说:不行啦,估计是个中篇小说,等下一期;
当下一期要截稿时,程永新给余华打电话,余华说:不行啦,估计是个长篇小说,再等下一期;
程永新想着余华肯定“怀了个哪吒”,等到第五期截稿日期时,余华说:还没写完,再等第六期;
就这样一直等,终于等到了长篇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。余华就是这样一个“不靠谱”的作家,在创作上他随心所欲,天马行空。
余华把写作看成一件轻松的事情,他说,只要认识汉字就行了。评论家洪治纲说余华的文字很简洁,余华把这一优点归结为自己识字太少。
余华,就是这样一个乐观的人,总能把缺点想成优点,把坏事想成好事。
医院的童年经历,让他看到了人间悲苦的一面,这样的童年经历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。
世界最初的图像就是在那时候来到我们的印象,当我们长大成人以后所做的一切,不过是对童年时就拥有的基本图像做一些局部的修改。医院的听闻,也许决定了他今后与故乡永远割舍不了的情感。
虽然余华离开了故乡,但他笔下都是故乡。从《十八岁从门远行》到《活着》,到《兄弟》,都出自他成长的南方小镇。故乡才是财富真正所在地,那是他内心永远安全的地方,所以他把写作比作回家。
余华的作品被人认为是暴力美学作品,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他的血液里流的是冰渣子,认为他冷酷无情。但生活中的余华和作家里的余华完全是两个人,一个是拿着泛着银光的手术刀;而另一个却谈笑风生、热情开朗。
这可能就是他认为的,写作对于他来说是另外一个世界。
在这个世界上,人倘若没有在苦难中看到好玩,在正经中看到可笑的本领,怎么能保持生活的勇气呢?余华看到了生活的苦难,但苦难从来不是他要歌颂的,值得歌颂的是在苦难中从不放弃的那些坚强已经苦难中的温暖。
余华认为作家是非常幸福的,因为一个人可能有很多的欲望和情感,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能全部表达出来,而一个作家可以通过作品把这种思想发泄出来。
这让我想到了他的座右铭:假如你不想被狗咬着的话,你就跑在狗的后面。
一个人不受名利、生活的束缚,而是在绝望发现希望,坏事中发现好事,苦难中找到快乐,无论经典的作品还是幸福的生活都会“娓娓道来”。
作者简介:一知半姐,有两个聪明可爱的女儿,一手带娃一手码字,喜欢文学和历史,
- 上一篇文章: 在海上漂了362天,我只想回家澎湃在线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