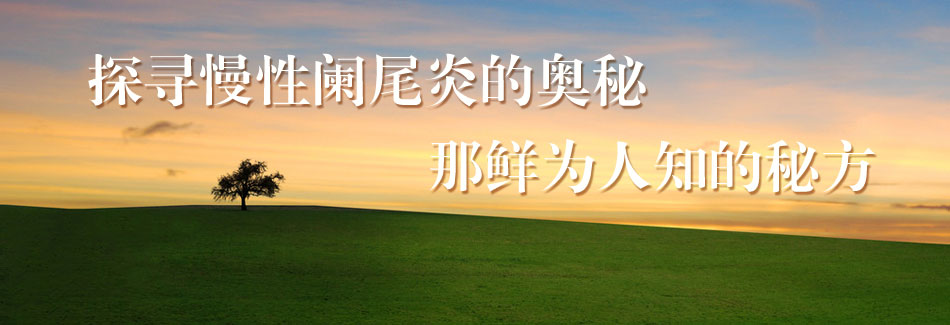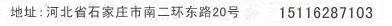王朔平生最恨伪君子,痛快做个ldq
年8月23日,王朔出生在南京。一转眼,这个“玩世不恭”的“顽主”已过六十。
作家刘震云说,鲁迅的小说,读来读去,说了两个字,吃人,后来王朔的小说,读来读去,也就说了两个字:别装。
作家野夫说:王朔笔下那些邪里邪气的小人物,油腔滑调的声口,表达的正是我辈对这个伪善的社会的反动。
平生痛恨伪君子,痛快做个“真流氓”
01
年8月23日,王朔出生于南京,原名王岩。上小学时,父母发现班上有个女孩儿也叫王岩,回家翻字典,翻到一个“朔”字,就给他改了名。
出生没多久,王朔就去了北京军队大院,成了所谓的大院子弟。他所在的那个院儿是军事训练部。父亲是军校部的参谋,负责教战术,一年到头很少在家。母亲是医生,俩礼拜回趟家,也没什么时间照顾孩子。一岁半,他被送进保育院,脑子里根本没有父母这个概念。
十岁以前,王朔都不认识爸妈。“我爸就是一军大衣,我妈就是一黑呢子大衣大衣。”大人们也懵,经常把他错认成自己孩子。很长一段时间,王朔都不知道自己是爸妈生的,还以为国家有个工厂,专门负责生孩子,然后丢在保育院里养活。
亲情的缺席,给了王朔自由,也令他多少有些怨恨。有次在学校,高烧40℃,送到医院急诊室一查,急性阑尾炎。当时,母亲正在给重病患者决定治疗方案,医院,做完手术的王朔躺在病床上,第一句话就问:“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看我?我做手术家里人都不来。”
后来母亲问王朔:“你能原谅妈妈吗?”
王朔说:“不能。”
△王朔兄弟与母亲
王朔是跟小伙伴儿们混大的。跟外面不一样,这帮大院孩子,从小玩儿的都是军事游戏,连扑克牌打得都是军事扑克。书呢,读军事电报,读《张国焘回忆录》《丘吉尔回忆录》,电影看军教片《奇袭》。打架,家常便饭,受了欺负,必须找机会打回来。王朔的攻击性和战斗性,早在那个时候就形成了。
第一次跟人打架是跟我哥一块儿。拿一根棍子,跟我们院一个比我大三岁的打。冬天,那孙子带着棉帽子。
我哥在前头跟他叫板,我在后面铆足了劲呱叽一棍子打下去。他回过头来看着我,没事。喔!给我吓的。他一推给我推一跟头。但不觉得寒碜,我觉得我是在有意磨练自己,将来我还得打仗呢。
?????????——访谈《我是王朔》
大院里的孩子,身上都有一股生猛的优越感,从小穿军服,觉得自己是保卫国家那拨人。上了街,都管外面的人叫老百姓。日后,从这里头走出来干成事儿的人也着实不少:
收藏家马未都,空军大院的;姜文,父亲是部队干部,从小就做英雄梦,所以至今自恋;拍《甄嬛》的郑晓龙,总后大院的;崔健,空政文工团的;“话匣子”许晴,外交部大院的,爸爸是贺龙的警卫员;叶大鹰,叶挺之孙,八一电影制片厂大院的,前身是“延安电影团”,专拍军事电影……
叶京,跟王朔一个院儿的发小,也就是《甲方乙方》里面那个作死跑乡下吃苦的老板,后来拍了《与青春有关的日子》,那是大院子弟的一部挽歌。他在部队时,坦克射击手第一名,说打你左眼绝不打右眼。蹲在他边上有个装炮弹的,那是《我爱我家》里的梁天。
对了,还有俩兄弟,也是大院出身,据说打架手特黑,后来他们搞了个电影公司,叫华谊。
△大院文化是那一代许多电影人的集体记忆
?
02
在北京翠微小学读书时,王朔就不是三好学生。上课时,他低着头不看老师,理由是那个女老师长得太难看了。写东西,他一直很自信。老师让写作文,他自己玩自己的,老师怒问:“你怎么不写?”王朔一抬脖子:“我打腹稿呢。”
?
在老师眼里,他是个特别反动的孩子。读初中的时候,老师上语文课,讲错了一个字,他忽然站起来:“老师,你那个字讲错了!”
老师很不高兴,没理他。
?
王朔还说:“老师你讲错啦!”老师冲门一指:“你给我出去!”
老师告诉王朔他爸:“你们家王朔上课老是不集中精神听课,还影响其他学生。”
此后,王朔看老师不顺眼,老师看王朔也不顺眼。最后没办法,王朔只能转学。所以在王朔心里,权威从来就不是不能质疑不能推翻的:“有知识怎么了?有知识了不起?有知识跟道德完善两码事,谁他妈都别假装是大师。”
水兵王朔
?
年高中毕业,王朔去青岛当了海军。当时的王朔长相清纯,一张娃娃脸,有点像女孩儿。但一笑,又能拧出点儿坏水来。他出名,因为特别能侃,中外军事典故、京城名人趣事、各种医学案例,张口就来。说到好笑的地方,能把睡上铺的人笑得铁架子床直摇晃。
?
3个月新兵训练,王朔就没怎么吃饱过,全是吃窝头,刚要睡觉,一声哨响又要跑八里地。与世隔绝,根本见不着女的。有次查脑膜炎,部队来了几个中年女大夫,这都能让新兵解馋。
坐汽车进青岛市医院。门口是女兵指挥汽车,打着小旗。我心里一阵惊喜。卫生队住的楼,那种青岛带洋味的小楼,一看,二楼站着一大排护士学员,哇!全是女的!
那儿的伙食也有肉末儿了。
?????????——访谈《我是王朔》
在《致女儿书》里,王朔回忆道:“我到部队在新兵连还尿过一次床。打了一天靶,成绩不好,又累又沮丧,晚上情景重演,幸亏天寒被薄,睡觉也穿着绒裤,没在床上留下痕迹。”
那时的王朔,已经有点儿皮了。队里开“批判四人帮”讲用会,别人都非常严肃,就他别具一格,稿子里掺杂大量北京方言和街头笑话,给众人逗得前仰后合。一个周末,他外出找战友聊天,回部队时,没钱买公共汽车票了,王朔灵机一动,调皮地把手上喝剩下的汽水给女售票员:“要不你把这瓶子拿去,还能赚点儿。”结果对方大怒,司机也怒了。最后王朔还落了个严肃批评。
其实王朔并无恶意,不过想开个玩笑。可惜被女售票员视为调戏。为此,王朔沮丧了好一阵,还问人家:“外边把我传成什么样了?”
可见他是个十分珍视名誉的人。
有趣的是,这和王朔日后在文坛激起的反应,极为相像。他只是想给大家开个玩笑,结果学院派当真了。而他也感到莫名的委屈。
?
03
改革开放后,优越感还在,社会变了。军人不再享有特权,不少人回城都傻了,不知道何去何从。高考恢复时,很多人意识到,这是改变人生的首选之路,王朔也不例外。
王朔智商高,但并不擅长考试。他在北京三里河附近报过一个高考补习班,穿一身军大衣,坐教室最后面,尽忙着跟女孩儿说话了。
年,王朔跟着朋友去了广州,当了一阵“倒爷”。到广州一看,有的士、有歌厅,人家的西餐比北京老莫和新侨地道多了。当时部队给了王朔块钱,让他买彩色电视机。结果他拿钱当本儿,到汕头倒录音机和电视,的录音机拿北京卖。
电视、墨镜、电子表,王朔全倒过。彼时,小说已经开始评奖,文坛出来一拨又一拨新人,王朔根本没把目光放在写作上:“小说有意思吗?在金钱面前全傻了。”
复员后,王朔被分配到药品商店当业务员,下乡推销药品。每个月工资36元。见过钱的王朔根本看不上。83年打击经济犯罪,把他抓了个正着。退赔,王朔没钱,只能从工资里扣,每个月30块。王朔一看,一个月6块钱我还活个什么劲儿?我去哪儿一个月赚不到36块钱啊?
辞职后,王朔跟人谈生意,每天夹个公文包满北京乱窜,没一次谈成的。他还想当出租车司机,也没当成。所有路都堵死了,最后没办法,想到早年在《解放军文艺》上发表过两篇小说,一拍脑门子:要不我当个作家吧?
那时候投稿,王朔是为了考大学读文科练笔的,写了个作文似的东西,叫《等待》,文字那都不能叫青涩,说是幼稚都不为过。结果投出去,发了。王朔心说:原来写作也就那么回事。
在药店工作时,他撞见一个同事看《解放军文艺》,跟人家说:“这是我写的。”同事说:“别逗了,你写的?这上面的都是作家。”王朔觉得特没劲,同事问:“你说你写的,那这篇小说多少节?”王朔答不上来,同事说:“完了吧,说不出来吧,人家作家都知道自己写的是多少小节。”
给王朔臊的。
过去我写过小说,认为这事很容易。这事对我来说确实很容易。辞职后,一段时间里我又写了10个短篇,但都被退了。这时我认识了一些青年编辑。被退回来的小说确实不是东西,所以退了对我没多大刺激。但是一切都不成了,到83年下半年,真的没任何事干了,不写小说就没什么出路了。
真没想到,后来,一不留神,成腕儿了。
——访谈《我是王朔》
年,发小叶京考上了首都师范大学,读了一年没劲,退学了。当时开饭馆要三个法人,他就拉王朔挂名,开了个饭馆,叫做“天府酒家”。
王朔没事儿就晃荡到叶京那里,人家前面吃饭,他窝在馆子后面写小说,后来还经常把《啄木鸟》的一帮编辑请过去吃饭,拉拢拉拢感情。八十年代的文学盛世,什么伤痕、先锋派、新写实一批批都要喷薄而出了,谁也没想到,王朔一出来,风头盖过了所有人。
04
年2月,《当代》杂志公布了上一年度当代小说评选名单,最末尾有个不甚起眼的名字,王朔。获奖作品,《空中小姐》。拿的是新人新作二等奖。一等奖,空缺。
《空中小姐》讲一个社会青年和空姐的恋爱故事,有些琼瑶式的肝肠寸断。但在当时,感动了不少青年男女。王朔写这篇小说,第一稿3万字,拿给编辑龙世辉,龙世辉一看:“好故事,就是太单薄了,你给丰富丰富。”
王朔挖空脑袋,给故事抻到了10万字,结果等他去编辑部,龙世辉退休了。又拿给章仲锷,章仲锷一看:“好故事,就是枝枝蔓蔓太多了,你再修改修改。”王朔跑回去,又来来回回改,前后改了9遍,加起来差不多万字。
根据王朔小说《永失我爱》和《空中小姐》改编的电视剧《永失我爱》
《空中小姐》稿费元,根本不够王朔吃的。他只能在社会上乱转,跟当时还在《青年文学》当编辑的马未都熟过一阵,常带着马未都跑北京舞蹈学校找女生神侃。晚上10点,人家女生都挨个儿洗漱完了,马未都实在扛不住了,王朔还挤眉弄眼:“再坐会儿,再坐会儿。”
一天下午,王朔请马未都过文艺生活:“舞剧《屈原》,一起去看吧。”马未都心想没什么事就去了,到门口,王朔就一张票。马未都问:“就一张票怎么看?”王朔说你甭管:“我有办法。”
马未都拿票进去,第一排,风光无限好。舞剧开始,只见王朔从后台出来了,把马给羡慕坏了。音乐声中,台上,演婵娟的女孩儿一个下腰,演屈原的背对观众,就势往前俯身。只听王朔醋溜溜地说:“估计丫亲了个嘴儿。”
青年马未都和青年王朔
演婵娟的沈旭佳,后来成了王朔的老婆。
头一次见面,两人互留电话,说无聊了可以打。真无聊了,就约在玉渊潭游泳,为了显得有内涵,各自把各自会背的名人名言都说了。当时两个人处境都不乐观,一来二去知了心。后来看了沈的舞剧,王朔就爱上了她。
王朔没正经工作,到处跟人找生意。这种待业青年在当时谁都不待见,叶京开个小饭馆,家里人都觉得丢人。于是,歌舞团领导找沈谈话,让她跟王朔断绝来往。领导劝说:“听说他是个流氓,乱结交女孩儿,这种人离他远点儿好。”沈说:“没事,他的事我全知道。”
追沈的也多,大款都有。沈根本就瞧不上。
那时我真是一天只吃一顿饭,每天猫在家里写稿子,希望全寄托在这儿上了。偶尔拿到一笔稿费,就满足一下沈旭佳的购买欲。我和沈旭佳都不会买东西,净上当,花冤枉钱。
我给她买的高筒皮靴,跟是歪的,她给我买的毛衣是桃红色的。最终还是常穿的那身衣服合体,索性一年四季地穿。反正沈旭佳在我眼里浓妆佳,淡妆亦佳,蓬头垢面不掩国色。
——访谈《我是王朔》年,《浮出海面》在《当代》第六期发表,写一个社会青年和跳舞姑娘甜蜜而惆怅的爱情故事。作者署名,王朔,沈旭佳。
?
05
紧接着,《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》发表,讲一个犯罪分子的爱情故事。三篇发表,虽说年轻人喜欢,但文坛就没正眼瞧过王朔。
王朔的爱情故事,男的都是城市青年,没啥正事,喜欢臭贫,蹭吃蹭喝,困顿迷惘,多少有他的影子。女孩儿呢,单纯、清澈,爱得死去活来。等到《一半》出来,有人不高兴了,批判声来了:有人在《啄木鸟》上撰文,说他笔下的男主角,没有任何正面的社会意义。
有人质疑:“这作者就是个流氓吧?”
甚至有个女编辑说:“我可不敢跟王朔约稿,我去了他要是强奸我怎么办?”王朔听了,嘴一咧:“你怎么那么瞧得起自己呀?”
王朔曾说:“我要一直沿着爱情路子写下去,没准儿就写成琼瑶了。”但不久后,他发表了一篇《橡皮人》,这是分水岭的作品,讲广州的经历,有点深沉了,第一句上来就是:
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时开始。
稿子寄给《青年文学》,马未都一读,太棒了,赶紧拿给主编。主编也说好:“但第一句话太刺眼,拿掉吧。”正巧刊印那天,马未都值班,在印场,马未都又给加回去了。这在当时是要冒开除风险。
好在没几天,《小说月刊》要转载,也没删这句。它就这么保留了下来。
多年后,叶京拿起这篇小说,加上《玩儿的就是心跳》《动物凶猛》,拍出了风靡一时的怀旧电视剧,《与青春有关的日子》。
还很青涩的白百何、文章
06
那天下着大雪,叶京开着车,拉着王朔从西直门去和平里影协的电影院。路上,王朔眉飞色舞地狂侃:“中国电影哥们儿现在平趟!”十几年后,叶京回忆起这段情景说:“他当初幼稚得就像一个孩子,放了很多狂话。”
?
年,的确够王朔狂的。那一年,他的四部小说被搬上银幕,分别是《顽主》《轮回》(改编自《浮出海面》)《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》《大喘气》(改编自《橡皮人》),因此也被称作“王朔年”。王朔的风头,一时无两。
尤其发表在《收获》上的《顽主》,王朔可以说旱地拔葱,自创了一种新文体,通篇充斥着“王氏幽默”的对话体小说,一路靠北京方言调侃下去。
表面特别不正经,下面,全是辛辣的讽刺,讽刺社会乱象,讽刺假道学,讽刺知识分子的端着,讽刺一切假崇高和自以为是的精英主义。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- 上一篇文章: 小柴胡汤,它的这四种神奇的变化,妙不可言
- 下一篇文章: 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