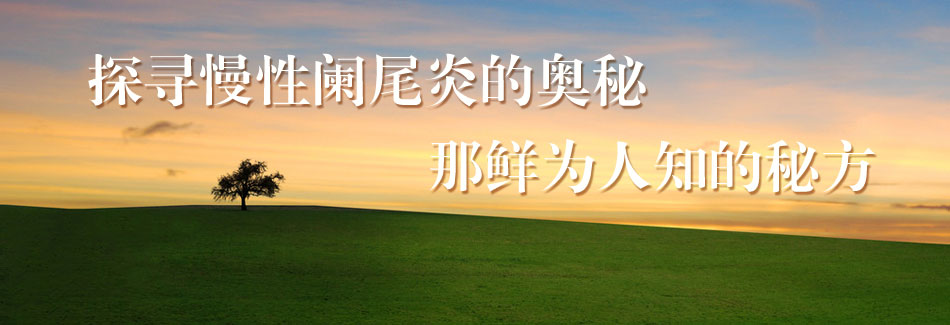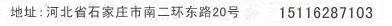散文一盏温暖的灯肖成年
一盏温暖的灯
文
肖成年
我开始怀疑大脑的可靠性,时间的河水把一些事物冲刷得模模糊糊,许多细节变得游移不定。之前,母亲总是笑盈盈地站在我的眼前,不知从哪天开始,她的笑容变得像镜头中那些无法聚焦的景象,即使强按下快门,也无法对准焦距。
感觉中,母亲一直是笑着的,笑容像黑夜里的一盏灯笼,在我的眼前时隐时现。
1
暑假很快过去了,我们的心还在田地里野,还惦记着蚂蚱、蜻蜓、蝎虎子。天好蓝,鸟的鸣叫清脆而婉转,窗外的世界无拘无束。从教室窗口望出去,太阳正挂在大殿的檐角,像一枚钟,仿佛轻轻一敲,会发出金属的轰鸣。鸽子的翅膀,正掠过大殿高挑的檐角,飞向云端。
学校建在一座用土筑就的庄子里,庄墙宽可走马车,内有一座年代久远的大殿,殿里供奉着彩塑神像,墙壁上绘着一些飞来飞去的人和兽。不知从什么时候,那堵庄墙开始被人们用镢头一点一点地往下弄土,弄了土垫牲口圈,或者掺进煤面子中抹成煤块烧。庄墙越来越低,但还是高过了我们的视野和童心。
母亲背过身去,一笔一画地写板书。野了一个假期的伙伴们开始做小动作,你捣我一下,我拍他一下。母亲偶尔回过头看一眼,笑笑,转过身继续写板书。
同学们不怕她,一点也不,就像我不怕她一样。一个假期过去了,同学们的嘴像是秋天的豆夹,管也管不住,话像成熟的豆粒一个劲儿地往外蹦。“孙老师”、“孙老师”,他们争先恐后地叫着、嚷着,要把积攒了满肚子的奇闻乐事一口气地倒给老师。母亲耐心地听着,嘴角抿着笑。有同学抢不上话,急了,喊出“妈妈!”我也急了,“是我妈妈,不是你妈妈。”同学们一阵哄笑,“是你的妈妈,咋不给你一个人教。”回家的路上,一脸委屈的我问母亲,为啥要教他们?母亲看着认真的我,笑得弓下了身子。
我怀念这样笑的还很年轻的母亲,仔细地回想她的样子。她的眉梢、眼角、脸庞以及满头的黑发,村庄、田野、小路;母亲牵着我的手,身后尾随着一只黄狗,夕阳的余辉……这一切晕染组合成一幅色彩沉着的画,永久地挂在我记忆的墙上。这样的母亲是幸福的,我不知道,是不是可以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只想着这样笑着的还很年轻的母亲呢。
小时候,很多比我大的孩子手里都有一个纸夹子,用来夹书,很好用,我也很想有,所以看到了,不管是谁的便拿回了家。回家找截棉线穿进夹子眼,高高兴兴地拎在手中。母亲看见,沉下脸,问我夹子哪来的。我支吾其词,说拾到的。她顺手拿起一根树条,不由分说,劈头就打,边打边喊:你再给我拾一个,再拾一个来,咋那么好的事让你碰上?一下子变得凶巴巴的母亲吓得我哇哇大叫,纸夹子物归原主,我对母亲的回忆也有了极力想忽略的东西。多年之后,母亲说起打我的那次,笑呵呵地说,小孩子不打,不知道啥叫拾啥叫偷。
母亲的心很大,大到不只是装着她的孩子们。有次,我和一个伙伴闹别扭,厮打过程中,竟发现他穿着我的裤子。我丢下伙伴去问母亲。母亲直截了当地说,是我给的,你有裤子穿,他没有。我感到委屈,觉得母亲不是我一个人的母亲,也是别人的母亲!。
母亲的学生里边,有一个女生,心里有事就会找母亲说。那女生的座位空着的日子,母亲就会去那个女生的家。那个女生的座位一直空着,母亲就会一直去那个女生的家。终于有一天,那个女生离开家,母亲再去那个女生家,身后再也带不来那个女生了。母亲多少知道了一些那个女生的事,当然,传说有很多个版本,一说那女生被家里人嫁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,男方是一个城里人;再一说,是那女生去城里的饭馆当服务员,挣钱贴补家用。
好长一段时间,母亲脸上少了笑容。
2
记忆里,母亲留着两个辫子,虽不粗,但也匀称。后来,她的辫梢越来越细,就索性剪成短发。剪了短发的母亲,开始了一种新的职业——村卫生所的一名赤脚医生。之前,村子里妇女生小孩,大都在炕上放几锨炕洞里烧过的草木灰,条件好点的会买几刀粗陋的麻纸,接生婆用一把剪刀剪断脐带,或者将一把铲子烧红,将脐带轧断了事。碰到难产,只能生死由命。
母亲有文化,被选去学接生。后来,乡人有个头疼脑热的,也来找母亲,小病小灾的,母亲都能应付得了。母亲积累了一些土方偏方,尤以幼儿方面的居多,十里八村的乡亲常常慕名而来。人们还是习惯叫母亲孙老师,而不是孙大夫。叫啥母亲都不在意,日日都是一张和气的笑脸。
村里人生孩子,是在家里,卫生所就巴掌大的地方,也无法容留生产。谁家的媳妇要生了,便早早地告诉母亲,母亲会定时去产妇家,听听,看看,问问,再细细地叮嘱一些事。真到生时,母亲背起药箱,风也似的往产妇家跑。边跑边安慰急得火烧火燎的产妇家人,人家慌,她是绝不能慌的。
民间的接生,凭的全是经验和耐心。说是要生了,可能一等就是小半天,不管黑天白天,母亲常常是戴着落日去,披着朝阳回。每次开门,看见的都是满脸倦容的母亲。
乡下,重男轻女的思想比较重,不管前面生了几个女孩,不生男孩不会停止。谁家都巴望着有个男孩,一旦又是女孩,产妇受气不说,连带着接生的医生跟着吃脸色。这时候,说服工作是必不可少的。遇上粗鲁人,不管三七二十一,摔门踢凳子,撒够了气才算了事。遇见不懂事的,仿佛是接生接的,分明是男娃,接出来的变成女娃了。母亲又不好讲理,闲气只能闷在心里。
在当时,生了孩子的人家,会在门外挂个用芨芨草编成的小筐,上面缝一小块红布,警示内有幼儿和生了孩子的女人。男人看了,不进屋,嫌生了孩子的女人脏,怕惹上晦气。我们兄妹三人,也避着母亲。母亲每接生过一个孩子,十天内不准做饭,即便是做了,我们也不吃。生了孩子的家里,大多会用方盘端上名为“擦手”的毛巾送给母亲,一条毛巾,就代表一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,母亲将各式各样的毛巾缝在一起做护被子,那被子像万国旗似的,仿佛母亲也将一万个孩子接到了这个光明的人世间。
田黄一晌。秋天,人们心急火燎,要把生长了半年的庄稼早早收进粮仓里。我家也不例外。但是,母亲随时都会扔下自家的活,不是出去诊病就是去接生孩子,家里外面,脚不停歇地跑。多数病人会聚来家里打针,我们一旦感冒,就抱怨母亲,是病人传染的。
母亲虚弱地笑笑,娃,谁让妈妈会这个,要不然他们也不会来找的。
3
母亲的身体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变坏的,或者,日子多上一天,母亲的身体就会变坏一天。母亲和我们,也就是她的孩子们,各自的人生仿佛朝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走着,我们不知道,我们的母亲会和我走得越来越远。
母亲身体开始疼,到底哪疼,她也说不清楚,我们更说不清楚。粗心的我们,开玩笑地对她说,以后不说哪儿疼,就说哪儿不疼。敏感的母亲以后就很少再说疼了,她不说,我们就以为她不疼了。
我偶尔回家,隐约地听说她到乡镇卫生院看病,乡卫生院的医生也诊断不清是阑尾炎还是胃炎,糊涂着开点消炎药就算了事。母亲说,她没事,人的命大着呢,哪能说病就病,小病小灾的,不怕。但是母亲身体里的疼痛并没有减少,一直潜伏着,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巨兽,终于在我新婚的前一天,越出笼子。
从老家赶来的父母亲,被安排在朋友的宿舍中,他们是来参加我的婚礼的。母亲到来的当天晚上,身体就有了发病的征兆。朋友急急地告知我,我赶到时,母亲脸上挂着笑也挂着汗珠。面对不安的我,她轻描淡写地说,没事,没事,快去忙吧。我将镇痛药、消炎药递给母亲,嘱咐她吃了,又去忙自己的事。
后来我知道,母亲那一晚,几乎被疼痛撕碎,原本隐藏起来的疼痛在那一晚无法遏制地爆发,大剂量的镇痛药吃进去,才算勉强维持着参加完我的婚礼。回家后不久,母亲又一次晕倒在刚刚收割过的麦地里。大夫们仍然诊断不出所以然,有的说是阑尾发炎,有的说是附件炎,直到有一天,一位妇产科大夫吃惊地说,你的肚子里有拳头大小的疙瘩!医院,仍无法辨清是囊肿还是实质性病变,那个潜伏了多日的疼痛在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的犹豫不决中疯长,等到十多天后疼得无法忍受才迟迟将它取出,可为时已晚。
母亲被人从手术室里推出来,麻药的作用还没有散去,看起来很平静,眉心舒展,除了脸色比较苍白之外,仿佛好人一样。我们一直守候着她,盼着她快点醒过来。终于醒了的母亲,仿佛从另一个世界回来。她的目光从我们的脸上一个一个滑过去,最后落在我怀中的女儿脸上。“快把孩子的鼻涕擦了!”这是母亲手术后说出的第一句话。
手术之后,母亲身上的疼痛丝毫没有减轻,反而加重了。癌变让母亲的肚子里长满了再也无法清除的毒瘤。每天靠镇痛剂维持着存活的母亲,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能现出少有的安详。每天大剂量的化疗药物,杀死母亲体内癌细胞的同时,也把母亲变得虚弱不堪。
我不敢仔细端详病中的母亲。病痛的折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但是,不管怎么样,我都想母亲活着,多活一小时是一小时,多活一小时我就有一小时是个有妈的孩子。我,父亲,母亲的所有亲人都在为母亲能好好的活着努力着,到处托人买很难买到的镇痛药。母亲也坚持着,无论多痛都坚持着,直到她痛得说不出话来的时候,我觉得自己紧紧抓着母亲的手应该放开了。我意识到,早早地离开,对母亲是最好的解脱。
4
我最早戴过的一只手表是电子表,那是在县城上学时母亲买给我的。记得是个周末,我刚刚入睡,隐约听母亲和父亲商量一件事,要不要买。睡意朦胧中,听他们说一块电子表要20块钱,是一个人从外地带来的。20块钱,当时对我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,父母亲虽有些犹豫,但母亲还是坚持从那个人手里买了这块表,这块使我拥有了精准时间刻度的表,一直陪伴我好多年。
在县城读书,两周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回一次家。在学校的吃食,以家中带去的烙饼或者蒸好的馍为主。村子里不通班车,只能求人代。每到捎吃食的日子,母亲便早早地候在路边。捎东西的乡亲对我说,你母亲真不容易,大冬天的,围个不挡风不挡寒的头巾,眉毛和头发上全是霜。
参加高考的那年,我把印有我名字的一本杂志拿给母亲,那上面虽只有我二十几行文字,母亲却是看了又看。我掏出几颗糖,放在母亲手里。这是用稿费换来的,分给同学们时给母亲留下了几颗。母亲口里含着糖,脸上带着笑,不停地问我:真是你写的吗?真是你写的吗。
那时高考还要预选,只有一部分人有机会参加高考。预选完毕,高考的日子就到了,恰在这时我患痢疾。不知母亲如何知道了消息,宰了一只鸡煮好,赶往十五里外的镇子坐车到县城来看我,而我正从县城赶往家中,我们在路上交错而过。母亲一宿未眠,次日又坐第一趟班车赶回家中。母亲几乎是滴米未进,煮好的鸡,一口未动。她抚着我头的瞬间,我心里酸酸的。我别过头去,硬是从嗓眼里把那股哽咽憋了下去。母亲已经哭了,我不能哭,我已经是大小伙子了。
乡邻听说母亲病了,医院探望。母亲出院回家后,家里几乎成了全村人聚会的地方,包括一些知道消息的外村人。乡邻们人前都是笑脸,人后个个长吁短叹。多年轻啊,为什么要生没法医治的病。没有答案,就像上天再也不能给我一个健康的母亲一样。
回家之后医院时气色好,母亲喜欢搬个小凳子在院子里晒太阳。那天早晨,天气晴好,太阳照在我们为母亲临时搭在院子的床铺上,母亲精神也比前些日子好了许多。从街门涌进四五个人,进门就说:“孙老师,你不记得我了吗,我就是那年那个被你救了的人啊!”母亲无力地笑笑,问:“你们家里人都还好?”河西走廊的太阳,无遮无拦,光线强得让人睁不开眼睛,母亲失血的脸孔在金色的阳光底下,竟显出几丝妩媚的气息。
5
阳光隐去,溶入黑夜的怀抱。一个电话,证明了一切恐惧都成为不可改变的现实。
九月底的老家清晨,寒霜闪闪。灵前摆着一张小方桌,小方桌上摆着寿桃、各式供养,还有干果,一只头没有割下来的羊蒸腾着热气,一只冠首有点发黑的鸡,一盏盛满了胡麻油的长明灯,一个堆满了冥纸灰烬的瓦盆……凄婉的丧乐,烈性的白酒,苍白的微笑,绝望的眼泪……这一切,都和躺下的母亲有关,这一切又似乎与她无关。
母亲温暖的笑容被定格在灵前。那张有着笑容的照片是母亲第一次手术后路过照相馆时照的。或许,那时她真不知道自己的病情,或许,她早已为这一天做了精心的准备。身为医生的母亲,对自己的病情应该再清楚不过。
不足三岁的女儿吟,尚不明白生与死是怎么回事,对着灵前的照片直喊:“奶奶!奶奶!”吟拉着我的手,非要把她奶奶叫醒,嚷嚷着奶奶睡了这么长时间,怎么还不醒?天上的云低垂着,阴冷而潮湿,泅湿了母亲的笑容。
院落里的那些农具,在唢呐乐器吹打的凄怆声和来来往往的人群中,静静地倚墙而立。那些农具,似乎还保留着母亲的体温:那把曾经陪母亲在瓦房城水库劳作的铁锨,已经磨得失去了锋芒;经年不用的那架勒勒车瘫伏在地,轮胎瘪了,辕条龟裂,生命的内容已被抽离……
送别母亲的时刻到了,村里人都出来送母亲最后一程。门口,呼拉拉地涌来本村的一群小学生,有大有小,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,为母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。那些孩子里,有不少是通过母亲的手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。孩子们以最虔诚的心向他们妈妈样的老师做最深情的告别。
母亲走了,我一直固执地认为,她没有走远。或许,她正在微微地笑着,在高空凝视着我们。从那时开始,我常有一种感觉,母亲手提一盏灯笼,正在漆黑的山岗上或者密林中,寻找回来的路。
来稿须知《新边塞》是纯文学治疗白癜风的小偏方北京哪里治白癜风最好
- 上一篇文章: 宝宝得了阑尾炎妈妈们请熟读并背诵全文
- 下一篇文章: 同济医院带你了解阑尾炎,脂肪瘤,腹股沟直